蔡燚:泌尿外科的一名小医生
编者按:科学的海洋中,每一项突破性发现都是对知识边界的勇敢探索。AME旗下杂志一直致力于挖掘和发表具有深远学术价值的研究,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医学领域的发展,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宝贵的指导。
为了深入挖掘这些研究成果背后的故事,我们特别邀请文章作者进行一系列深度访谈,为广大读者呈现科研工作的独特视角和深刻洞见,展现他们的学术理念和人文思考。我们相信,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,他们的经验和智慧能够启发和激励更多年轻人,帮助他们在科研之路上找到自己的方向,实现自己的价值。
本期,让我们一同走近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蔡燚。
采写| 陈童
蔡燚:泌尿外科的一名小医生
“我是泌尿外科的一名小医生”,这是蔡燚最常挂在嘴边的自我介绍开场白。
别看他自称“小医生”,就以为他资历尚浅。恰恰相反,在泌尿外科领域,他已默默深耕多年,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。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,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投身临床工作;从一头扎进罕见病领域艰难探索,到全力投入常见疾病的诊疗;从默默积攒每一份临床数据,到建立前列腺癌专病队列......桩桩件件,满是探索与坚持。
对他而言,“小医生”不只是个称呼,更是一种自我警醒。它时刻提醒着自己,无论收获多少成绩与赞誉,都要守住从医初心,保持旺盛求知欲,不断学习、持续进步,绝不能因过往成绩而故步自封。
关于这位“小医生”这些年的从医故事,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先完成再完美
2020年,我开始探索前列腺癌临床及转化研究领域,此前我并未专注于此。
前列腺癌作为男性群体中高发的恶性肿瘤,早期诊断对于提升后续治疗效果、改善患者预后起着决定性作用。然而在临床实际中,早期前列腺癌症状隐匿,缺乏典型表现,筛查手段有限,这些因素相互叠加,导致大量患者确诊时已处于局部晚期,甚至发生远处转移,治疗难度大幅增加。
传统的超声、磁共振扫描、CT扫描和骨扫描等影像学检查,在检测前列腺癌及其转移灶时存在局限性。为突破这一临床困境,寻求更高效的早期诊断方法,我们科室联合核医学科、放射科和病理科,组建了前列腺癌多学科诊疗团队,开展前瞻性临床试验。
在研究中,团队比较了双标(PSMA GRPR)PET/CT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刺、多参数核磁共振(mpMRI)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刺、系统穿刺及联合穿刺等不同方式在前列腺癌诊断中的效能。
结果表明,双标PET/CT引导的前列腺靶向穿刺,诊断准确率高于mpMRI引导的穿刺。并且,双标PET/CT靶向穿刺联合系统穿刺,不仅能确保不漏诊临床显著性前列腺癌,提高诊断率,还能让近半数患者免去前列腺穿刺这一有创检查。
2021年,这项研究成果发表于《欧洲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》(European 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Molecular Imaging),这也是我在该杂志发表的首篇文章,后续该研究及系列研究还获得了“湖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”的支持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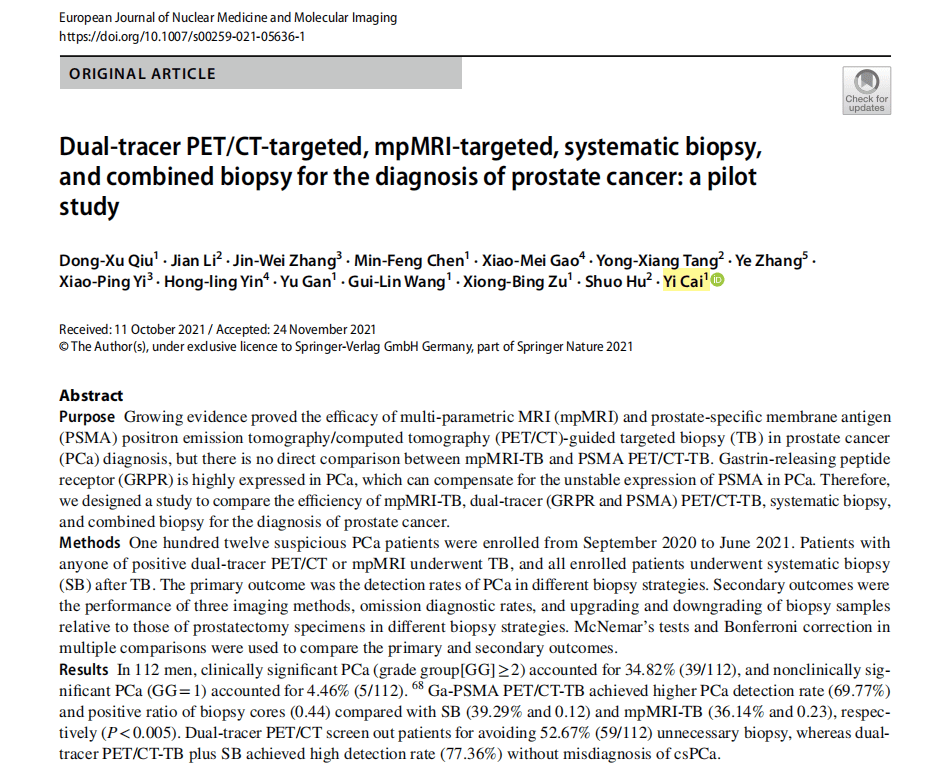
尽管我们对该研究进行了内部和外部验证,但受现实条件限制,总体样本量依然较小,模型性能有待进一步验证与提升。即便如此,这次的“完成”,也依旧是很关键的一步。
完成这项研究后,我又紧接着开展了两项新研究,预测终点一致,但在方法层面大幅优化。扩充多中心数据并引入机器学习方法,显著提升了预测的准确性和说服力。目前,这两篇新成果正在投稿过程中。
事实上,每一次的“完成”,都是朝着“完美”的一次靠近。如果一味陷入对样本量绝对充足、研究设计无懈可击的空想式等待,那么后续一系列基于此的研究便难以推进。恰似是那些在有限条件下成功“完成”的成果,层层累积,才搭建起通往更深入、更精准研究的阶梯。
暂别小众
2020年以前,我的研究方向并非前列腺癌,而是结节性硬化症(TSC)。TSC是一种罕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全身疾病,会引发神经系统、皮肤等多方面症状。
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,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李汉忠教授和张玉石教授。当时,张教授已在TSC研究领域探索多年,察觉到这个领域仍有诸多空白亟待填补,便建议我投身其中。我领会其用意,欣然应允,就此选定TSC作为博士研究课题的方向。
TSC-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(AML)是TSC最常见的肾脏病变,超过80%的TSC患者都存在这种情况。博士期间,在导师的指导与帮助下,我与团队开展了国内第一项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治疗TSC-AML的II期临床试验。
最终研究结果显示,依维莫司不仅能够显著缩小AML的体积,还能有效改善患者因TSC引发的全身性症状。相关研究数据促进了依维莫司治疗TSC-AML的国内适应证获批。
凭借这项为临床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依据的研究,我得以在AUA和EAU年会上分享成果、展示进展。2017年博士毕业后,我顺利获批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”,还成为2020版《结节性硬化症相关肾血管平滑肌脂肪瘤诊疗与管理专家共识》的执笔人之一。当时,我深感荣幸,在共识执笔人当中,我是唯一的住院医师,其他几位都是资深教授。
后来,为了推动TSC相关知识与诊疗技术的普及,我时常参加TSC主题病例巡讲活动,泌尿外科领域不少老师和同行都是通过TSC相关工作认识我的。直到2020年初,我都是将TSC作为临床科研的核心方向。

图4 临床工作中的蔡燚(左一)
其实,读研时这个想法就在我心底“种下”了。但我知道,这件事做起来绝非易事。有想法是一回事,真正做成又是另一回事,还得等待合适的时机。
在中山大学读研时,我参加过一场小型学术会议。会上,业内大佬提到一年内完成了大几百台手术,打算整合相关资料用于论文发表或课题申请。这一思路瞬间点燃了我的热情,令我印象深刻。可惜,多数时候会议结束就没下文了,没人真正去落实。即便有人尝试推进,也常因资料不全而受阻。从数千例数据里筛选,最后能用的可能就寥寥几百例,甚至更少,这极大拉低了研究起点。
博士毕业后,我来到长沙工作。在各类学术会议上,我依然能听到类似的倡议与论调。虽说大家都明白建设专病队列的好处,可真正付诸行动的,少之又少。
直至2021年11月,我的第一篇“欧核”(European 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 and Molecular Imaging)文章发表,那时我手头已积攒了可观的数据量。我意识到,行动的时机成熟了。
2022年1月,我正式开始前列腺癌专病队列建设工作。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专病队列,完善的临床信息与规范的生物样本缺一不可,二者相互支撑,为后续深入研究打基础。
一开始,我搭建起Chestnut EDC系统(Electronic Data Capture System,电子数据采集系统),专门收集患者临床信息,像临床症状、影像检查结果、病理诊断详情、各项化验指标等,事无巨细。以门诊工作为例,经手的每位患者,我都会详细书写电子病历,文档通常有两三页。我把每个病例都当成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的罕见病案例,这大概是研究TSC带给我的好习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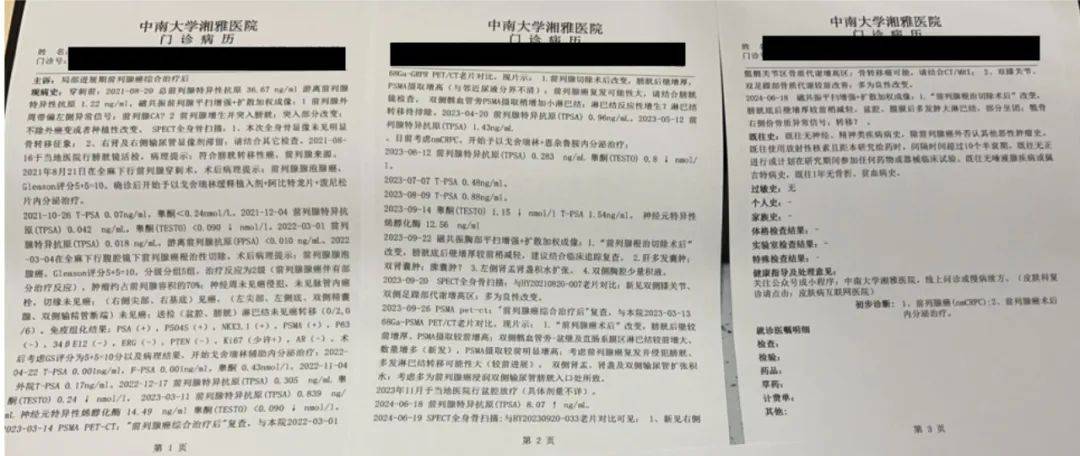
图6 蔡燚在2025年第40届欧洲泌尿外科年会(EAU)上分享研究成果
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,湘雅医院泌尿外科的齐琳教授、陈敏丰教授等一众老师和前辈,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与支持。每一次与他们交流,都让我受益匪浅,前辈们站位高、视野广,在他们的引领下,我渐渐有了底气,开始勇敢尝试曾经想都不敢想的事。
我现在时常想,要坚持去做一件又一件有意义的小事。哪怕一年做成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,五年完成一件稍有分量的事,十年达成一个更具价值的目标,这都是好的。如果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既定工作流程,那实在没意思。真正有意思的,是在工作中不断突破自己的认知边界。
一开始,我们的认知范围或许像一个直径仅10公分的小圆,局促又有限。随着每取得一点突破,这个圆的直径就能向外拓展1公分。长此以往,新理论、新认知便会不断涌现,这正是科研的核心价值与魅力所在。
我特别喜欢一句话:人在未来五年、十年,乃至临终之际,感到后悔的往往不是做过什么,而是那些想做却没做的事。所以,究竟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?时间会给出答案。我现在所做的一切,只求五年、十年后自己不会后悔。
其实,有这份坚定信念支撑,便没什么可惧怕的,放手去做就对了。
专家简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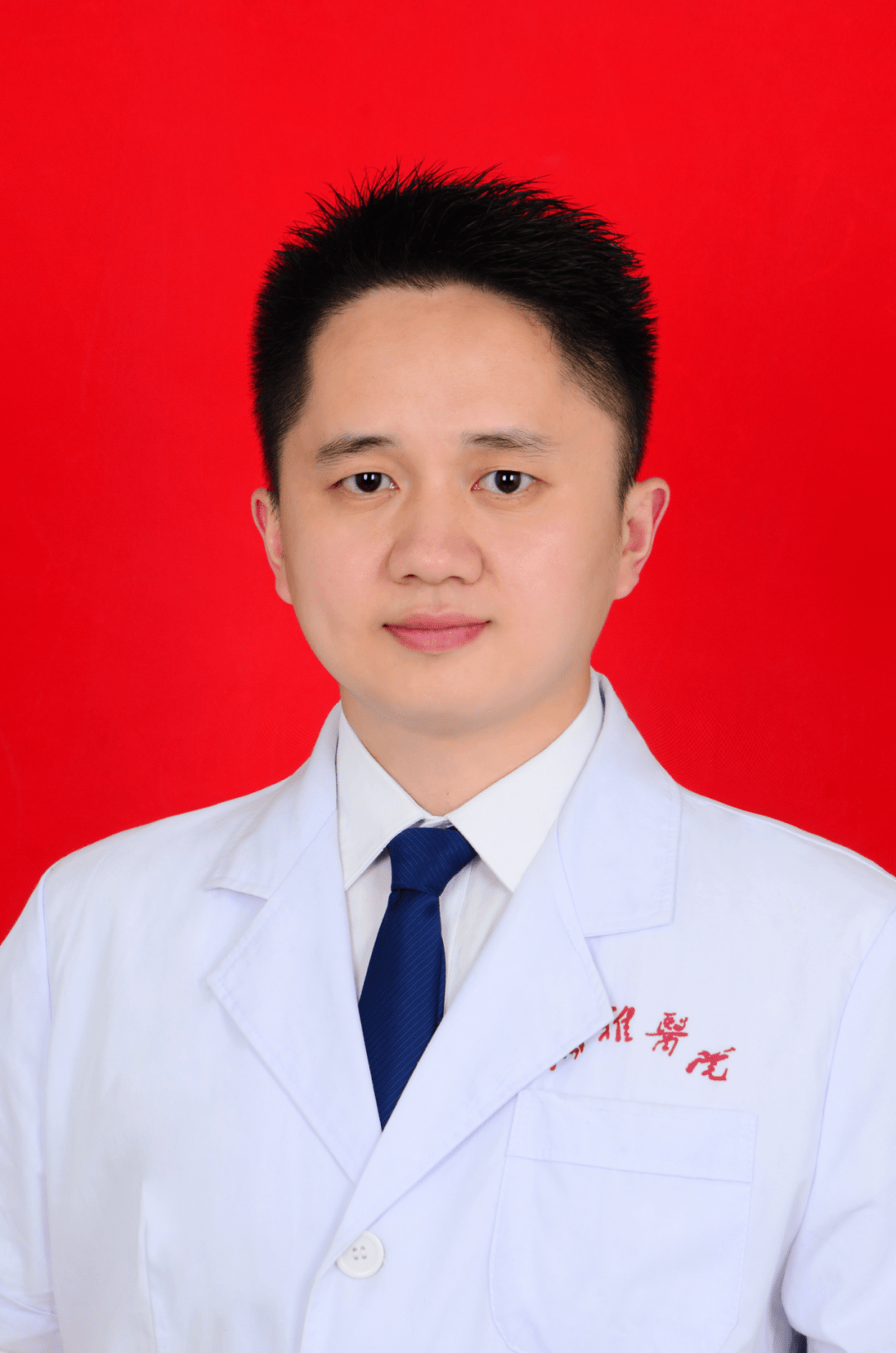
蔡 燚
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泌尿外科
副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、湖南省杰青
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(CUA)基础学组委员
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(CRHA)泌尿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
中国医师协会泌尿外科分会(CUDA)数字与人工智能学组委员
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泌尿肿瘤青年医师联盟成员
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》青年编委
致力于前列腺癌的精准诊疗和转化研究,代表性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of Urology、Journal of Nuclear Medicine和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》等国内外知名期刊,多项研究在ASCO-GU、NCCN、ESMO-Asia、EAU和AUA等国际会议上进行展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