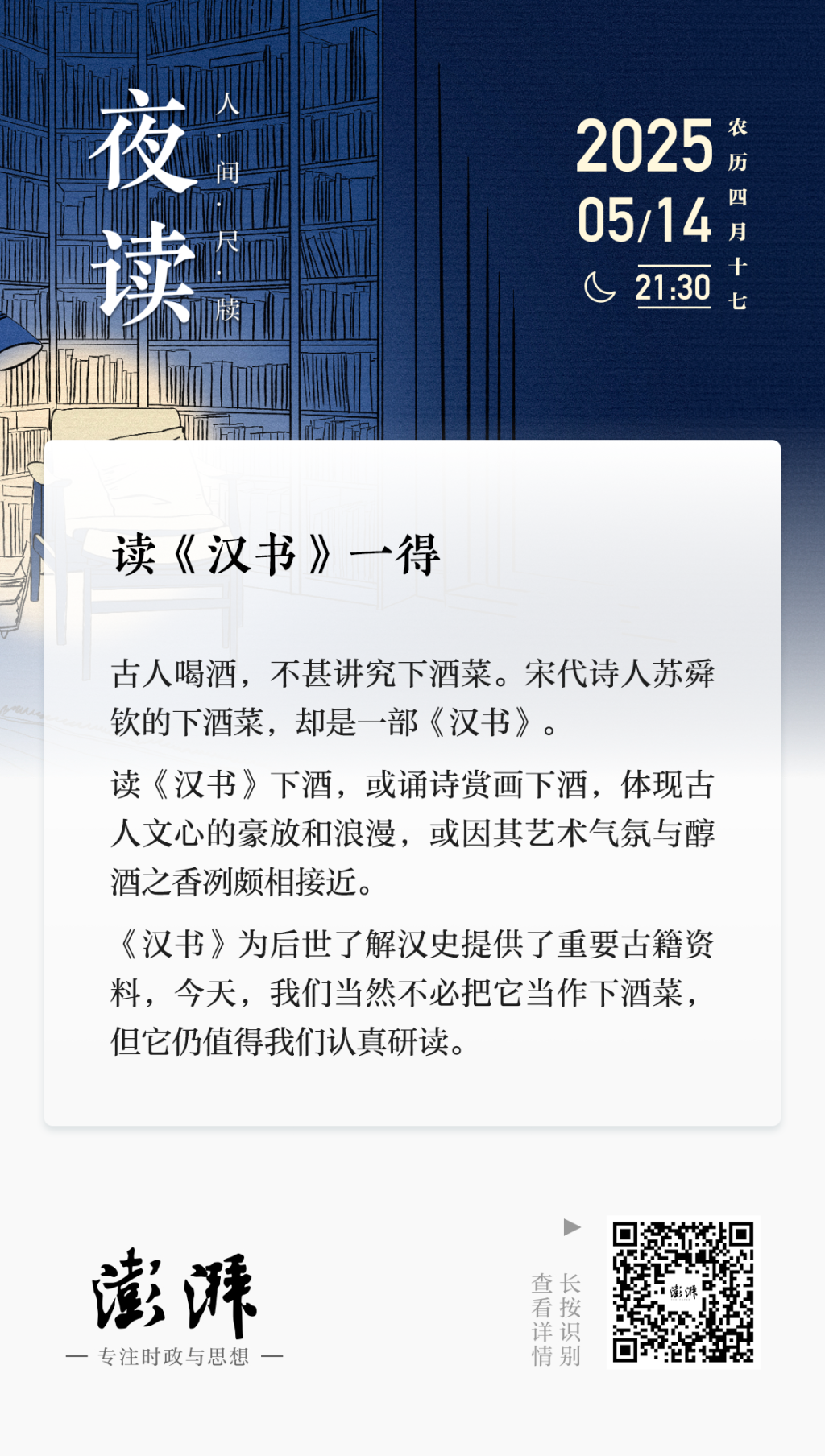夜读丨读《汉书》一得
古人喝酒,不甚讲究下酒菜。“花生就酒,越喝越有”。在众多的下酒菜中,花生米是酒桌上的常客,如果再加一盘拍黄瓜、一碟豆板,就相当不错的了。
但是,宋代著名诗人苏舜钦的下酒菜,却是一部《汉书》。他住在岳父杜衍家中,每晚读书要饮一斗酒,却不用下酒菜。杜衍感到很奇怪,偷偷地去张望,只听见他在朗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。当读到张良狙击秦始皇,误中副车时,就拍案叫道:“惜乎夫子不中!”说完满饮一大杯。岳父又听他读到张良与汉高祖遇见时说:“此天以臣授陛下”。他又拍案叫道:“君臣相遇,其唯如此!”说完,又满饮一大杯。他岳父看到这种情景后大笑道:“有这样的下酒物,一斗实在不算多也。”这个故事传诸后世,“《汉书》下酒”则成了一个著名的典故。
宋代的一斗酒,是多少分量昵?据悉,宋代的一斗酒为2400毫升,约合今天的4斤8两。这一斗酒,不是今天的53度茅台白酒,也不是绍兴加饭酒,而是低度的水酒或米酒。否则,满饮两大杯,就可能醉到了。
以读书佐饮者,古人所在多有。陆游也是一边看书,一边饮酒。他在《雁翅峡口小酌》一诗中写道:“欢言酌请醥,侑以案上书。虽云泊江渚,何异归林庐。”清醥,指的是清酒,也是低度的水酒。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《桃花扇》的第四出《侦戏》中也写道:“且把抄本赐教,权当《汉书》下酒罢。”由此可见,从宋代到清代,读《汉书》下酒,已成不少读书人的习惯。
除了读书可做下酒物,诗画也可以作下酒菜。明代文人沈璜在《题沈启南奚川八景图》诗中写道:“奚川八景不可见,尽情敛取入画图。”“读书有此下酒物,秫田可酿钱可沽。”说的是,欣赏画图中的奚川八景,也可以作为“下酒物”。清代文人屈大均《吊雪庵和尚》诗中,亦有“一叶《离骚》酒一杯”之句。屈大均读“惟草木之零落兮,恐美人之迟暮都”两句,饮清酒一杯,其味也无穷。清初名臣陈廷敬谈到他读唐诗下酒的情形:“夜酒一壶,直钱四文,无下酒物,亦不用箸筷,读唐诗写俚语,痛哭流涕,并不知杯中之为酒为泪也。”陈廷敬也是性情中人,读唐诗读到感人之处,眼泪落入酒杯,也变成了酒。
苏舜钦饮酒读《汉书》一事说明,作为正史的《汉书》,曾具有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文化魅力。读《汉书》下酒,或诵诗赏画下酒,体现古人文心的豪放和浪漫,或因其艺术气氛与醇酒之香冽颇相接近。这种情趣,既是古人饮酒不忘学习的风雅表现,又表现出了古人饮酒的豪放和浪漫不肆的铺张之风。
因为《汉书》写得好,更有甚者,有人将它放在身边,甚至挂在牛角上,随时取读。《旧唐书》记载了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出行时,骑在牛背上阅读《汉书》的故事。《旧唐书·李密传》写道,李密“乘一黄牛,被以蒲鞯,仍将《汉书》一帙挂于角上,一手捉牛,一手翻卷书读之”。蒲鞯,即用蒲草作坐垫。李密乘一黄牛,在路上和越国公杨素行路相逢,杨素见此大为惊异,乘马追行,感叹道:“何处书生,耽学若此?”又问所读何书,李密回答说:“《项羽传》”,于是李密大受杨素器重。这一情节流传久远,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所作《蓟门送李子德归关中》诗中也提到此事:“常把《汉书》挂牛角,独出郊原更谁与?”
《汉书》能当下酒菜,又能挂牛角,因史事的惊险和叙事的魅力,使《项羽传》和《张良传》得以与“牛角”、“酒壶”合构为故事的重要条件。《汉书》中《项羽传》和《张良传》的记述,都出自《史记》。当代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在《司马谈作史》一文中写道:“《史记》一书,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之部分有二,一为楚、汉之际,一为武帝之世……若楚、汉之际,当为谈所集材。谈生文帝初叶,其时战国遗黎、汉初宿将犹有存者,故得就其口述,作为多方面之记述。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,惟谈为当首功。其笔力之健,亦复震撼一世,叱咤千古。”班固写的《汉书》,也因 “其笔力之健”, 叱咤千古。
班固编撰《汉书》,历时二十余年,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。其中《汉书》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,《汉书》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。班固编撰的《汉书》,是《史记》之后我国又一部较为完整记录史实的著作,成为二十四史之一。《汉书》为后世了解汉史提供了重要的古籍资料,今天,我们当然不必把它当作下酒菜,但它仍值得我们认真研读。